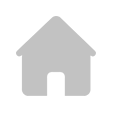中 文 摘 要
封建制国家其权力基本是专制主义的,它能实行一定量的吏治,但却永远消除不了因专制权力不受制约而产生的腐败。封建国家的吏治,比起真的的民主制来虽都有局限性,但这二者毕竟也有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是人类社会权力制约历史上的里程碑,它对于大家国家打造新型的权力制约规范,具备参考借鉴意义。
几千年来,封建刑律在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上有丰富的经验,大家今天欲从立法及司法上加大对现行刑法中“渎职罪”的研究,使其进一步健全,古刑律中这方面值得总结和借鉴的地方颇多。
古时候对官吏在司法审判上违法犯罪的监督比较全方位,综合起来有惩治不依法判决的犯罪、惩治不依法审理的犯罪、惩治司法官吏不依法刑讯的犯罪、惩治司法官吏不依法实行判决书犯罪、惩治越权审断及违法受理诉讼的犯罪和惩治司法官吏监禁囚犯方面的犯罪。
1、国内古时候司法审判中的职务犯罪概述
(一)中国古时候惩治司法官员职务犯罪的特征和意义
司法官员的职务犯罪是刑法中的要紧内容之一,古时候是如此,近现代是如此,以后也仍会是如此。
职务犯罪所以要紧,这与其犯罪主体是官吏这一点密不可分。官吏是国家政务活动的要紧参与者及管理活动家主要推行者。官吏的职务活动是国家职能推行的主要杠杆。官吏依法履行职务是国家法制确立的要紧基础。官吏守法对民众守法起着带头羊有哪些用途,官吏的坏法是对民众违法犯罪的鼓励与唆使。对官吏 违法犯罪姑息容忍最容易激起人民群众对法律的逆返心理。官吏违法犯罪所形成的对民众的压迫与他们导致的腐败的环境,是社会上违法犯罪的根源之一。
司法官吏违法犯罪的一个特征是可以借助职权。以借助职权为特点的职务犯罪,比一般犯罪有更大的害处性。一是职务犯罪侵犯的客体总是是是国家法益的管理秩序;二是由于有职权可借助,其犯罪得逞率高,后果紧急;三是由于凭着权力,这种犯罪对被侵犯对象的反抗与举报,客观上都存在抑止性;四是这种犯罪常常表现为国家机构内部的一种腐烂,富于隐蔽性,因而容易避过普通的监督。历史封建刑律都看重对职务犯罪的监督是有其深刻缘由。
封建国家对司法官吏职务犯罪的监督与处置,根本目的是强化国家机器,提升封建国家的统治效能。但封建刑律对官吏违法犯罪的抑制也有其相对的进步用途。在封建社会,人民与专制政权的矛盾集中地反映在官吏与民众的对立性上。封建统治者为了缓和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常常奉行的手段之一就是用刑法方法来监督官吏,使官吏对民众的欺压与剥夺限制在民众可以容忍的限度之内,从而来缓和封建国家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便是封建刑律维护封建吏治的积极意义。
看重吏治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思想,用刑法来惩治官吏的职务犯罪的封建刑律的一个传统特征。封建刑律惩治官吏职务犯罪的特征是在立法上张起严密的法网,法律对职务犯罪不但从严监督富有威慑性,而且在立法和司法上具备肯定的预防性及教育性。
(二)中国古时候司法审判职务犯罪的渊源
司法审判活动是古时候国家非常重要不能国务活动之一,也是古时候官吏职务犯罪中较主要的一个方面。
司法官吏在审判上的职务犯罪史书早有记载。《尚书•吕刑》曾指出西周法官有对犯人不可以依法定罪判刑的“五过之疵”。其内容是“惟官、惟内、惟货及惟来”。孔安国《传》解这五个方面是“或尝同官位,或诈反囚词,或内亲用事,或行货枉法,或旧相往来”。《吕刑》中还记载说,司法官因犯为些罪过,而致出入人罪的则“其罪唯均”,即与犯人同罚。这段史料了解地概括了当时司法官违法审判中的主要犯罪表现。
在中国,职务犯罪也是一项古老的犯罪。历史告诉大家,官吏的职务犯罪基本上同国家与法律的产生而同时产生。
古时候中国关于官吏职守的专门立法,出现得也非常早。国内商朝已经有了为预防和降低官吏(包含国君在内)违法犯罪而专门制定的法律《官刑》。《尚书•尹训》记载国相伊尹说制定《官刑》的目的是儆戒有权的人物:“制官刑,儆于有位”,达到“居上克明,为下克忠”的目的。商朝的《官刑》中,规定有“三风十愆”的罪名,从作风上、道德上、政治上来管束官吏和当权者。所谓“三风”是指“巫风”、“淫风”、“乱风”。其中“巫风”包含无节制地在宫室歌舞(“恒舞于宫,酣歌于室”)的“二愆”。“淫风”包含徇私于财货和女色,长期地游乐和狩猎(“殉于货、色,恒于游、畋”)的“四愆”。“乱风”包含轻侮国君的命令,拒绝忠直之规劝,疏远上高德劭之人而亲近狂顽之徒(“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的“四愆”。训令还指出:“唯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作为臣下的人,如不匡正君主杜绝“三风十愆”,则要处刺脸的“墨”刑。惩罚官吏的职务犯罪是国家管理活动的需要。官吏职务犯罪的内容及规范,伴随国家政务管理活动的进步变化而进步变化。国内西周有关国家管理活动的立法已有不少记载。
《周礼•秋官•大司寇》规定最高法官“大司寇”的职责之一是“以五刑纠万民”。其中“二曰军刑,上命纠守”,“四曰官刑,上能纠职”,意即便用于军中的“刑”法,是鼓励遵守命令的,举论有亏职守的;实行于官府的刑罚,是鼓励贤能,举论失职的。这样来看,在先秦海量的吏治立法中,包含有一系列惩治官吏职务犯罪的法律规范。
从立法的角度说,封建社会初期,官吏职务犯罪的法律条文都散布于刑律的各篇之中。战国魏国的《法经》六篇中是职务犯罪的“金禁”与“博戏”被列在《杂律》之内,其他《囚》、《捕》二篇内当然也会包括职务犯罪的内容。从秦简的片断中可以断定,秦朝关于职务犯罪的法律条文也散列于“六律”之中。《置吏律》及《行书》中在规定官吏的某些职务犯罪时都说“以律论之”。所谓“以律论之”就是以《六律》中的规定办。汉朝的《九章》及汉律六十篇中,也无专门的职务犯罪的篇章,职务犯罪的条文散列于各篇的状况可以想见。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职务犯罪在封建刑律中渐渐形成单独的篇章。在明清规戒律刑律中职务犯罪规定得齐全,监督得严密,在编纂上条分集中,安插科学,继续体现了封建刑律看重吏治的优良传统。
2、国内古时候司法审判中职务犯罪的表现
古时候对官吏在司法审判上违法犯罪的监督比较全方位,综合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一)惩治不依法判决的犯罪。
通过审判给罪犯定罪判刑,古时候较早就有在这方面监督的法律规范。凡不依法判决,其违法行为都依据不一样的主观心态来定罪处置。
1.纵囚 秦律中说:“当论而端弗论,及埸其狱端令不致,论出之,是谓‘纵囚’。”即应该处罪而故意不处罪,与减轻罪行,故意使被告够不上处罚标准,从而判令无罪,就是“纵囚”。纵囚罪刑罚较重,一般要以被纵囚犯之罪罚来处罚纵囚之人。
2.不直 秦代把仅限于肯定幅度范围内的故意错判称为“不直”:“罪当重而端轻之,当轻而端重之,是谓‘不直’。”即罪应该重处面故意轻处,应该轻处而故意重处,是是“不直”。
汉代“不直”的定义与秦代不完全一样,其表述是“出罪为故纵,入罪为故不直。”在“故意”的首要条件下,只有在“入罪”的状况下,汉代才称为“不直”。秦代的“不直”,汉代以“不实”对应。
3.失刑 在秦代与属故意“不直”相对应的过失地在幅度上处刑不当的行为称为“失刑”。《睡虎地秦墓竹简》上记载一位审判官吏把“六百六十”的赃误订为“值百一十”。在定性时,上级回话询问说:“吏为失刑罪”,但“或端为,为不直”。这里界限比较了解:过失的错断为“失刑”,有意的错断就属“不直”。
4.出入人罪 司法官吏不依法判决之犯罪,各依其犯罪 主观心态区别罪名,在规范的比较严密的是唐代。按《唐律疏议•断狱》规定,唐律第一一般地把审判官定罪判刑上的违法行为统称为“出入人罪”。然后“入罪”与“出罪”又各分为“故意”与“过失”二种,共四种:故意入人罪,故意出人罪;过失入人罪,过失出人罪。在出入罪的幅度上又区别为出入“全罪”及出入轻重的不同状况。所谓出入“全罪”是指无罪判有罪,有罪判无罪,与从笞杖入徒流,从徒流入死罪的各种状况。是出入轻重的是指在刑等上从轻入重、从重出轻,与笞杖之差及徒流之差的出入。在追究审判官的刑事责任上,法律规定,故意入全罪,以全罪论;从轻入重,以差额论;故意出罪的状况,也参照此原则办理。但,过失地入罪的,比故意犯“减三等”;过失地出罪的,比故意犯“减五等”。
5.不具引律令格式正文 唐代需要法官在定罪判刑时,要完整地抄引有关的法律、法令的正文为依据。如此规定是便于监督依法判决。《唐律疏议•断狱》:“断狱之法,须凭正文。若不具引,或致乖谬。违而不具引者,笞三十。”作为断罪依据的法律条文不但要引正文,而且需要完整地抄引。这种规范在晋朝已开始打造。
[1][2]下一页